周榕:专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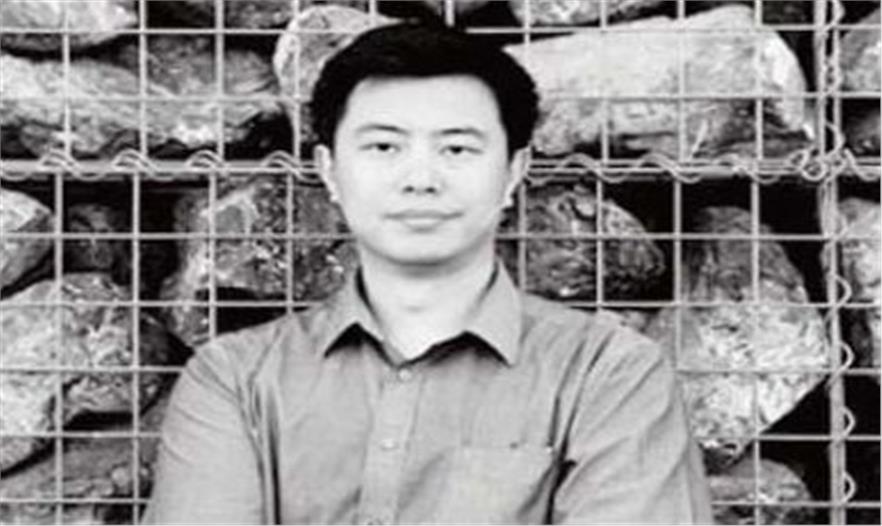
周榕,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硕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2001年至今,周榕与建筑大师关肇邺先生一起,主讲清华大学研究生“建筑评论”课,以“微城市观”、“微建筑观”、“微批评观”为基础建构起独特的城市与建筑评论体系。
LAC:因为您多重的身份—教师、市长助理、设计师,您对于“设计与研究”这个话题一定有很独到的见解。您在今年6月“艺文中国设计论坛”中提及过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当建筑与艺术沦为设计之后,产生了若干分离:设计者与现场的分离,设计者与使用者的分离、设计产品与文化传统的分离”,您是否认为设计与研究之间也存在分离?
周榕(以下简称周):要想谈设计和研究这个话题,必须要搞清西方文化的特点,尤其是西方现代文化的特点,才能理解西方为什么如此重视研究。西方现代文化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就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这已成为它的一个文化范式,一个驾轻就熟的思想套路,也就是说西方文化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文化”。它在面对任何一个认知对象时,无论大小,都必须先找出一个或一组问题来,然后将这些问题—“解决”,或貌似“解决”,一个思想周期就结束了。在这种“解决问题”的思想范式下,所谓的研究就是找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
2 0 0 3年我刚跟张永和合作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他的工作方式基本是西方的寻找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模式。所以张永和有一句名言:“建筑不是创作”。他认为设计就是研究,这是他最核心的设计观。其实我个人并不完全赞同这样的一个设计观念,因为我认为面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思想和行动,并不仅仅只有寻找问题和解决问题这么一种单一的途径,还有很多自由创造的可能。我觉得不能简单判断说研究型设计就是正确的,非研究型的设计就是错误的,这里没有高下之分,对错之别,只有选择不同。这个世界理应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作为创造世界的设计师,并不需要把自己的设计方法统一在一个固定的模式里面。
“设计作为研究”这种思想套路,我觉得对于以前不经研究和思考,甩开膀子就干的“中国式设计”来说,起了一个很好的纠偏作用,但也不能矫枉过正,对其奉为圭臬,应该给那些自由思想的设计师留下一些个人空间。
“研究型设计”有一个好处,就是它适应模式化的大生产,西方的现代建筑教育是与建筑的现代生产体系相一致的。设计的目的与建筑生产的目的高度一致,都是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问题解决了,设计也完成了,设计的成功与否取决于问题解决的巧妙程度。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的西方现代建筑史可以被称为一部“问题史”,而当西方社会从“问题社会”逐渐转型,“问题供给”开始匮乏时,习惯于解决问题的西方设计师只好自己给自己设立问题,“没有问题创造问题也要上”,这时的设计就开始沦为一种思想的打靶游戏。
研究型设计更多关注的是客体的规律,这样无形之中就把主体的情感与设计过程分离开了,设计者不再是富于情感、性灵、机趣,并且充满瑕疵、软弱与盲点的凡人,而是一部以问题为原料,并不断生产出解决方案的神性机械。外部世界因研究而变得越来越透明,但我们的内心却因为研究而越来越模糊,这是科学解决不了的事情。
LAC:跟您刚说的研究模式有点差异,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只为发现问题,目的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为研究而研究,不是为设计而进行,设计师能够借鉴这些研究成果,这样一个过程不是由设计师一人来完成的。
周:的确,设计师所谓的研究基本上属于“二手研究”,更多的是通过书刊报章、媒体网络等渠道获得一些间接信息,这种“图书馆模式”的研究代表着研究者与现场的分离,在客观上也加剧了设计者与现场的分离。不过,二手研究也总比不研究要好一些。
LAC:通过这样二手研究方式,我们失去了对本真的直接认识,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设计师通常会抛出很多似是而非的观念,比如天人合一、绿色等等,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周:我跟你们的想法有点不太一样,我并没有一个先在的判断,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我不能用预设的判断去污染对现象的观察。所有现象的存在,我都觉得蛮有意思的,我只是喜欢去观察这个现象,去分析这个现象,当然也有可能会利用这些分析的结果。
建筑师自从学了建筑以后,就慢慢地跟现实社会脱开了。建筑师们其实不太了解这个社会的真实运行,他们熟悉的是一套理想的、乌托邦化世界的构成规律。这样的世界只是极少数精英一厢情愿的理想世界,但现实社会的血肉之躯注定无法栖身于高度理想的水晶框架之内。设计师越想营造一个理想世界,他越努力工作,就离真实世界越远。我敢保证多数建筑师们并不懂真实世界,因为他们只关注于现实世界庞大链条体系里面微不足道的一个环节,他们所研究的所谓“建筑本体规律”,跟众生所迷恋的这个红尘世界有什么关系吗?我们处身的这个世界是如此的乱七八糟,如此的丰富多彩,如此激动人心也如此让人失望,但是跟建筑师的工作都没什么关系。我觉得中国设计师的问题,第一是脱离社会,第二是没文化底蕴。因为建筑师绝大多数都是从工科院校培养出来的,中国的理工科院校第一是脱离社会的乌托邦情结最浓厚的地方,第二是最缺乏人文熏陶的地方。
LAC:您觉得建筑师为什么会跟社会孤立、跟文化脱节?
周:我觉得主要是教育。
LAC:这是不是您选择除教师外其他各种不同身份的一个根本原因?
周:是啊,就像一个游戏里面多种角色扮演。我经常尝试戴上不同的面具,用各种不同的角度,观察这个世界,时间长了,你会看到世界逐渐呈现出一个立体的状态。我觉得每一次角色扮演看到的世界都不太一样。所以不要带着目的去研究,不然你就会忽略目的之外的那么多好玩儿的东西。不管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当代教育,其实都是急功近利的教育,因为就是在不断告诉你各种目的。目的性太强的过程,就会失去了趣味,失去了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现在既不赞同中国的方式,也不赞同西方的方式,特别是对西方的方式越来越警惕,因为它貌似科学和理性的范式却更具有欺骗性。
LAC:您刚刚已经解释过西方的范式,能再概括一下中国的范式是怎样的逻辑吗?
周:中国范式我觉得还是很典型的—就两个字:对付。所以中国文人最大的特点就是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知道东西很多,但不执著,也没有一个超越性的终极关怀。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科学?就是功利层面能够把它对付了就行了。所以中国人最喜欢的叫做“摆平”,摆平不是解决问题,摆平是一种对付着的平衡态。中国式“摆平”和西方的“解
决”有着本质的区别。
LAC:您为什么非常赞成一种无目的的学习方法?
周:因为有目的的学习方法会把你束缚住,把你的视野限定在很小的一个地方。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忘掉这些方法,或者你知道这些方法但并不完全依赖于它。尽管有一些基本的方法必须掌握,但关键是在这过程中,你并非把自己刻板地固定在一个轨道上,而是保持一个开放状态,而且要不断积累、不断改变。否则的话,只是盖了房子而已,并没有提升什么。盖了10年、20年,房子都差不多,当然技巧可能熟练了一点儿,工程问题解决得更好一点儿,但是对于世界的认识并没有提高。而且,量变会引起质变这个观念我是不同意的,因为量的积累根本不会增加质的变化,质变依靠的是内心的觉悟。
LAC:所以您早在1997年与栗德祥先生合写的《建筑教育中有关创造性问题若干误区的探讨》就提出了设计师需要具备创造性思维。
周:虽然这是十几年前的研究成果了,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我特别反对在建筑设计里面提概念,概念是一种思维,而非想象。只有想象才能把情感、把非理性的东西调动起来,然后把它变成一个“生命状态”。只有当一个概念衍生、创造为真正的实体,才可以称为真正的设计,而对学生来说,从创造性思维到创造性想象之间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现在学生最大的问题,就是想了一个主意,然后就觉得设计已经做完了。
LAC:这个鸿沟的形成,是不是由于创造性想象力的匮乏?
周:当然!创造力和想象力不是一回事。唯有想象力才能让我们凭空创造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有生命的,特别是有着生命细节的。就像米开朗琪罗到一个采石场去,看到一块大理石,他说我能够看到我要雕刻的那个对象就睡在这块大理石里面,而我所做的工作就是去掉那些多余的部分。这是什么能力?这是想象能力,跟创新没关系。
让我们看看窗外,这窗户外面感人的东西是什么?绝对不是对面庞大的楼房,而是这几片叶子还没有掉,在11月末的风中飘来飘去,光线穿过树叶缝隙透进来,那光映在墙上,有点儿枯黄,有点儿绿,这是一个掺混了复杂暖色的冷冷的秋日。如果一个建筑师失去了对生活的感悟能力、失去了想象,就失去了如何把一个生命世界的细节变得丰满起来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概念再多,也只会是枯燥无味的概念。
LAC:物化能力,是不是也是属于鸿沟之一?
周:物化能力就是从你的脑子到手头表达的能力。建筑师随着实践过程的增多,这个问题大多能比较好地解决。物化问题主要针对教育,尤其是低年级的学生可能对此有些障碍。
LAC:您曾经说过,因为80后、90后是生活在消费社会中的一代,所以他们缺乏生猛的批判劲头。在您的教学过程中,怎样把他们的生猛劲挖掘出来?
周:我并不依靠一个固定的套路,而是因材施教。90后从小的物质生活已经相当丰富了,精神上没受过摧残,没受过打击,尤其考上清华的孩子,一路上都是天之骄子。我的办法就是先打掉他们的自尊,打掉这些虚幻的自尊,用不可阻挡的方式让他们彻底丧失掉对自己已有经验的那点自信心,把自己先倒空了,然后再反复揉搓他脑子这块抹布。这个过程就是要激发他生命中本能的东西。
消费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无论有什么欲望都可以通过消费的方式得到满足,商业社会是有需求就有供应,而消费社会是通过超量供应煽动需求。在消费社会中,就连人的欲望都成为稀缺之物,现实生活不能满足你的欲望,还可以通过虚拟的方式超量消弭,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对社会没有什么不满,他们的青春期是平静的。我觉得对现实的不满和野心对年轻人来说不是什么坏事。批评、社会批判的思想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一个基础。没有愤怒的社会,没有批判的社会,听不到多样声音的社会,是最恐怖的社会,哪怕看上去是再光鲜亮丽也是腐朽的,一切乌托邦都是腐朽的。而我的思想内核是反对一切形式的乌托邦的。乌托邦就是以一种虚构的理想状态的名义,去抹杀一切与理想状态有偏差的不同状态。
LAC:您读过乌托邦三部曲的小说吗?
周:当然。
LAC:我认为社会发展到最终,就是像小说描述的那样,也许只是我们现在正走在通往乌托邦的路上而已。
周:很有可能是这样。因为整个所谓的现代化就是一个乌托邦化的过程。为什么?现代化的基础是什么呢?是理性主义。认为人可以通过理性安排自己的命运,但理性能够关注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因为现代科学不关注人类的内心,它关注的是客观存在,乌托邦发展的结局就是高度科学化的生存,控制你的技能,控制你所有的想象力,那你还有什么意思?你活着还有什么尊严?所以我是觉得科学给我们提供的是完美的世界,这就直接导向乌托邦。到什么时候人类才能彻底省悟,我们需要生活其中的其实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
LAC:我认为设计师是除哲学家以外最接近乌托邦的人。
周:可能得反过来,哲学家是除建筑师以外最接近乌托邦的人。建筑师是乌托邦的缔造者和维护者。乌托邦是静态的、完美的、不容更改的,这是古今中外最残忍的、以最美丽的名义但却造成了最大破坏的一种学说和理想。
LAC:设计这个行业就带有一定的乌托邦的理想性质。
周:建筑师不说100%,99%都是乌托邦主义者,因为他要创造一个完美的小环境,不管大的社会、城市环境如何,他所建造的那个建筑都要具备所谓的完美性。但真实的生活不是这样的,生命本身并不完美,有健康的时候,也有生病的时候,你不能否认生病的时候就不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乌托邦仅仅为这个社会极少数一部分精英的极少数最佳状态而准备。比如巴西利亚号称是一个完美的乌托邦城市,但是仅仅离它10k m就有一个巨大的贫民窟,为什么?就因为必须牺牲一大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一小部分人的乌托邦梦想。所以现代设计被乌托邦绑架了,对不完美的世界视而不见。乌托邦是完美、合理、纯净的,但是不完美的世界该由谁来负责呢?
原文摘自《景观设计学》2010,(14):65-67









发表评论
热门评论